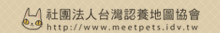認養人注意:
台灣認養地圖為網路送養刊登平台,提供公益送養資訊刊登服務。
認養細節請參考上列訊息逕洽認養人聯繫,本站不介入送養雙方,感謝您的使用,並歡迎您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
我的街貓朋友 公貓們 【聯合報╱朱天心】
我的心好痛喔,在這每天都有天災人禍、人命百條千條死去的現下,我簡直無法對別人傾訴一隻街貓的離去和與我的短暫際遇……
這是我陸續寫了半年的貓書《我的街貓朋友》的最終篇。
我遲遲延捱著不寫,自己清楚知道是害怕那文末句點所代表的曲終貓散,害怕那許許多多與我際遇或實可想像的街貓們,只因不及被寫到,就真如牠們在這城市角落不為人知的真實處境般的被遺忘被淹沒了。
這 本書,不同於前書《獵人們》的歡快恣意,因我必須意識到動保社運的處境(所關懷的是弱勢中的弱勢,是沒有選票的)、愛心媽媽志工們的非人辛酸、意 識到主 管業務公部門徘徊在進步(以TNR取代現行捕捉撲殺政策,T-trap捕捉、N-neuter絕育、R-return置回)或回頭路的關口,意識到社會絕 大多數人對流浪動物的冷漠輕心(人都活不下去了還畜牲?!)、意識到為數仍眾日復一日在殘酷大街求生的流浪動物……我無法裝可愛的只寫那少數幸運被人寵幸 愛顧的貓咪,我妄想要一一捕捉記下牠們街頭暗巷的身影、故事,證明牠們確實來過此世此城一場。
曾經我在〈獵人 們〉文中言及無可取捨公貓們與母貓們的情感表達方式(如確如刻板印象的,大公貓通常傻乎乎的在你腿上亮肚皮完全信賴的大睡;母貓們, 就算鍾 情於你,也不過在各個角落目不轉瞬的凝望你,謹慎的從不一次釋出所有情感和信任),這個不同在做了絕育手術之後更加明顯。我們屋中目前有貓十八隻,屋外例 行餵食照料的近四十隻(全已絕育),是個可堪觀察的田野。
於是有此觀察:母貓們絕育後,對人族不時撿拾來的孤兒奶貓全無興趣,第一時間退避書架頂或牆頭(雖然探索頻道播過的紀錄片裡野貓聚落的年輕母貓會幫忙撫育母親或親族所生的小弟小妹),母愛一點也不像傳說中的是與生俱來的。
照顧小奶貓的責任於是落在人族……嗯,和公貓身上。
大 公貓(當然並非每一隻)很快都能都願意克服畏懼並逃離仔貓的機制(機制的設計是為了保護幼獸免於大手大腳粗魯輕疏的傷害吧),前往嗅嗅、探視,進 而舔舐 喵喊媽媽的小傢伙,把屎把尿,夜晚與之共眠……這些記憶裡媽媽曾經對自己做過的事,乃至於人族在燙奶瓶、溫水、量舀小貓奶粉時,牠皆一旁全程注視參與,以 致有時我手邊另有事在忙時,真想拜託牠們接手咧。
大公貓的照顧幼小,似乎是社會性的,是為了物種己群的延續壯 大,牠們甚有公德心的耐心教導小孤兒貓生存狩獵技能,帶牠們四下遊盪認識周遭環境、獵食 (蟑 螂、蜥蜴、小鼠),接手原該貓媽媽做的所有事。牠們的社會化甚至高度發展到與共居一屋頂下的人族,牠會代表貓族老小與人族社交,發展出違背動物本能的複雜 行為,例如乳乳與辛亥白爸爸。
先說乳乳,牠原名乳牛,不用說是黑白花,這款貓特有的聰明,早晚會有像朵麗絲萊辛 為之特別寫的專書《貓語錄》。乳乳與姊姊小三花是2004年在里裡 的慈惠 宮小廟前的水溝裡發現的,起先以為是兩隻溝鼠,因皆渾身癩病加油汙泥,後來經我們一整個月的投藥餵食,姊弟倆復原成健康美麗但仍膽小難近的貓。我曾在〈只 要愛情不要麵包的貓〉文中描記過小三花,她右眼被一大塊三角形黑毛覆蓋,蹲在金爐上等我餵食時像個神氣的獨眼海盜頭子,我永遠記得,「臨終時,光速閃離我 視網膜的畫面,必定有這樣一幅。」
小三花不見後,我們決心在那農曆年勢必廟前鞭炮大作前把乳乳抓回家。乳乳很快 長成骨架身量偉岸的美男子,牠愛上人族謝海盟,天天尾隨上三樓,三樓內 已有神 經質貓三隻不能再增加,進不了屋的乳乳只得在陽台短牆上叫喚,牠是超讚的男低音,又唇上一撇黑鬍髭,我們總笑盟盟:「你的拉丁情人又唱情歌啦。」
其後,是家裡貓口增長最快的時刻,我們總說家裡留的都是醜的、病的、弱的、殘的,總之就是不可能送出認養的,其實只要小奶貓待上兩天,就不捨送人了,我真佩服那些長期做中途的志工,他們的心臟一定不同。
小奶貓的到來,屋中所有貓才聽喵聲就四下逃散一空,簡直的誰是鼠誰是貓啊,只有乳乳,立即接手貓媽媽工作,牠身量巨大,起起坐坐費盡工夫喬姿勢唯恐壓到共眠的小貓,牠又每每屈身亦步亦趨尾隨四下探險的小貓,我們總心存感激的笑牠婆婆媽媽笑牠娘。
乳 乳在貓界一定領有專業保母證照,經牠手的小貓無一不健康平安長大,有時牠帶小貓夜訓整晚累了睡大覺(總有那麼一次,彷彿成年儀式,貓媽媽或貓保母 會將小 貓帶至遙遠處,而後考驗牠們似的置之不顧自己先回),我們搖醒牠質問: 「券券呢?」(消費券時期來的小公貓),乳乳老神在在繼續睡,待我們婦人之仁再再催促牠,牠跳門出去,半個小時內帶回券券。牠且知道人族對每一隻貓的命 名。
牠與母貓一樣,該放手讓小的獨立時就放手(大多數人族都做不到),不藏私,不要求回報,一直到丁丁。
丁 丁是某夏天突出現在隔壁丁家院子的小孤兒母貓。丁丁長得又圓又甜(我們也叫牠丁圓甜),但驚恐膽小,智力不足到不辨利害安危,牠僅剩的智力額度就 是認準 貓族乳乳、人族我,我同情牠,總給牠加餐,偏心到屋內貓只要我喊一聲:「阿丁咕回來啦!」就紛紛前來,知道有白金罐可吃了。
丁 丁成年好久,乳乳知牠獨立難生存似的都不丟窩,影子或大尾巴般的帶進帶出,擺明是關門弟子。但其後我們仍收過幼貓(黃豆豆、橘子、券券),乳乳每 見沙發 角落擺著裝小奶貓的箱子,便發愁對之嘆氣,無奈的看我們一眼,那意思再清楚不過,因在場人族都異口同聲撫胸保證:「發誓這是最後一隻。」
乳 乳除了當保母,也身兼家中貓王,家中的公貓們雖都結紮,但三不五時仍會吵架爭鬥,無非你占了我老位子我故意行經你地盤,乳乳從不浪費任何精力在這 茶壺風 暴上,牠說到做到,在帶大券券後,帶著丁丁在隔巷人家開疆闢土,這家車庫那家後院把原落腳的街貓們打得無容身處。那些街貓,已被我們結紮,也取得居民們的 理解TNR,接受牠們出現在環境中,唯乳乳與牠們對峙叫陣時的聲量像瑞士山區長號一樣,不須鄰居們電話:「你們黑白貓又在吵架了!」我們自己都聽得到,三 更半夜都得快快披衣去排解。
乳乳變得只能每日傍晚匆匆回來吃一頓,又一刻不歇的繼續出門去捍衛牠辛苦打下的海外殖民地。對此,我們不領情極了,總在牠跳門進屋時挖苦牠:「了不起了不起,又打了白嘴巴和橘gay gay了吼。」
乳乳聽出語氣不善,哀怨的望著人,一雙綠眼睛企想懂得人族到底在想什麼。
與人族有了來往,無法回到純粹本能機制行事的狀態,彷彿神話故事中的混沌被鑿開了七竅倒地而死。被鑿開七竅的還有「辛亥白爸爸」。
看 名字就知是出現在辛亥國小的白(白底小黃塊,典型的「興昌亞種」)公貓,三年前發現牠影蹤時牠們其實是一家族,白爸爸、白媽媽和已懷孕的白小孩。 牠們的 活動領域介於國小和約二十多公尺外的「小坡庭園」社區間。會知道,是家住「小坡」的劉克襄告訴我的。原先白爸爸家族是克襄繼《野狗之丘》後觀測並打算書寫 的對象,後來因我們的介入、結紮、每日餵食,不再「自然」了,克襄便不再追蹤。
是的,我們的介入,白爸爸會在每晚我尚離小學老遠的牆外時,便那頭知曉哇哇大喊。牠會在天氣好我去操場跑道散步時尾隨我腳際邊走邊聊,牠是我在〈興昌亞種〉結尾說的那隻辛亥國小夜間校長,我的野蠻好朋友。
是 牠們因近親繁殖皮毛皆不佳故嗎?我像早有預感似的跨過界,揪起牠後頸至可依胸前(以便於日後萬一要送醫時才捉得到)。通常,我們極力避免與街貓發 展這關 係,免得牠們對不可測的人族失掉戒心。因為很弔詭的,等你察覺你在餵食照顧的街貓食慾不佳甚至不吃了,因此擔心牠生病想送醫時,唯一能誘捕到牠的方式是食 誘。牠不吃了,抓不到牠,你得忍受或長或短一段時間目睹牠想吃而不能,怔怔蹲一旁,而後終有一天不再出現的嚴酷過程。
是我有預感嗎?每次揪起白爸爸將牠抱在我胸口的那短暫片刻,我總低聲告訴才四、五歲的白爸爸:「把拔,將來我會帶你回家養老。」
如同前面說過的,街貓的逝去,除了遭車撞遭人毒這類的橫死,要有所謂的老死、病死、餓死、弱死,牠們都會靜靜的找一神祕角落「關燈」。但我們也觀察到,有些街貓,接觸過或與人族有了感情的貓,便會喪失掉這個本能機制似的。
所以,我們帶過好幾隻這狀態的街貓回家,「收留她,協助她去世。」這話是賈西亞馬奎斯回憶童年時一名投奔來家的年長親族的用語。我們給牠在屋裡布置一個寧靜幽黯不被打擾的角落,不做人族力求自我安心而做的侵入性的灌食醫治。
牠們大多一、二日內在我們淚眼中睡姿離去。
我完全沒想到對白爸爸的承諾這麼快就得兌現。白爸爸送醫時不意外的是腎衰竭,這在終生喝不到一兩口乾淨水的街貓來說是基本款病,之所以如此急轉直下,事後追想是國小圍牆工程動工了太久,雨後積水上都浮著油汙或各種化學溶劑,我們置的乾淨小水罐在酷暑總無法支撐一天用量。
白爸爸在吳醫生處住院十天,確定病情,我們又陷入兩難,強力治療(每天打點滴、針劑)可延長數月,但最終仍須面臨抽搐痙攣和劇烈頭痛,最主要的,那是家貓的醫治,對於一隻終生自由在街頭,但凡有一絲體力便企想回街頭的街貓,要介入到底?還是鬆手?
盟盟提醒了我們一道底線:「若不能醫治到牠可重回辛亥國小,就不要勉強。」
我們決定接白爸爸回家「關燈」,在父親書桌底下布置了暖軟不受打擾的窩,白爸爸立即接受,大多時沉睡,只在我們不放棄搖貓餅乾罐時會搖搖晃晃走出來。曾經,漠漠大氣中,每晚聽到我們餵食的搖餅乾聲是至福的事吧。
我們也把牠帶到前陽台,梅雨前風中所有植物混雜的訊息一定跟不遠處辛亥國小的差不多吧。我告訴牠:「都在著(這世界),你放心。」
五天後,白爸爸沒走,我們聆聽了各個包括在照顧腎衰竭貓小虎的翠珊的意見,決定帶白爸爸去吳醫生處,計程車上,我用一條美麗的大手帕蒙眼大哭。這手帕是四月在復旦大學時楊尹寧送的,白爸爸來後,我以它拭淚,不洗不換,因為知道最終要它做什麼。
吳醫生細細診察後,說:「放牠走吧。」
我揪起白爸爸,置我胸口,就像我們尋常在辛亥國小的夜晚,吳醫生靜靜的打了針。
天文用淚水濕透的手帕把白爸爸包好,納棺師不厭精細的為白爸爸做了今生牠最後一個也是唯一的窩。
我的心好痛喔,在這每天都有天災人禍、人命百條千條死去的現下,我簡直無法對別人傾訴一隻街貓的離去和與我的短暫際遇。
每晚,我仍得去辛亥國小餵僅存的白小孩和橘兄弟。沒有了白爸爸的校園,深秋一樣的好肅殺荒涼啊,我總對之暗暗自語:「白爸爸,我有做到帶你回家養老吼。」
【2010/07/10 聯合報】